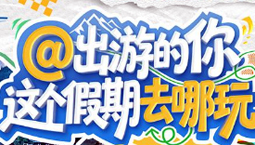悬崖边,古生物学家卢米斯纵身一跃,将即将坠落的风神翼龙DNA取样瓶救下,自己却身陷危境:他艰难地扒住岩壁,试图爬上悬崖,但随着绳子断裂,岩石松动,只能随着落石向身后的丛林坠落。局面虽岌岌可危,但观众并不会因此感到过分紧张。毕竟,作为电影的主角之一,卢卡斯仿佛手里攥着“免死金牌”。果不其然,在随后的全景镜头中,雨林中的树木顺利托住了卢米斯,并使他刚刚好地坠入了山谷中的水潭。接着,一个富有引导意味的空镜头,随着水潭涟漪消散的节奏缓缓推向岸边。镜头甫一静止,卢米斯便骤然浮出水面,英雄归来。甚至,连脸上厚重的金属边框眼镜都不曾掉落。
以上,是《侏罗纪世界:重生》中大约四分之三处的一段情节。按照好莱坞经典的三幕式结构,此处对应的应当是第二幕结束,此后将是短暂的平静与最后的高潮。影片的发展合乎预期:当卢米斯一行人重整行囊,带着历经艰险所取得的三种恐龙DNA样本踏上归途,最后的挑战——变异恐龙的夜袭与团队内部的决裂——便接踵而至。作为“侏罗纪宇宙”的最新力作,《侏罗纪世界:重生》讲述了一个老套却标准的好莱坞冒险故事。上映不足两周,该片便跻身2025年全球票房榜前十,斩获2025年中国进口片票房冠军,展示了其在商业上的亮眼表现。
只是,对于电影而言,商业属性与艺术价值、票房业绩与口碑评价之间,往往并不存在天然的协同关系。《侏罗纪世界:重生》虽然讲了一个合格的故事,但细节上仍有诸多瑕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卢米斯的“眼镜”。在影片中,这副眼镜不仅可以承受翻滚下坠的重力和游出水潭的阻力,还能抵御大海的风浪,逃离恐龙的追捕和袭击。眼镜在全片唯一一次离开卢米斯,是他触碰到温顺的泰坦巨龙,流下激动的眼泪之后主动摘下的。卢米斯的眼镜具有一种类似游戏的设定,它的“不可掉落”属性,与《我的世界》中“击杀凋灵骷髅有1/3概率掉落煤炭”的设定,以及《黑神话:悟空》中目之所及却无法穿越的“空气墙”具有同一性。只是在游戏中,这样的设定约定俗成、合情合理,是构成游戏“规则”所必需;但在电影中,这样的设定就显得有些悖于常理。
这是电影制作团队的疏忽吗?显然不是。“穿帮”在电影中虽然并不少见,但通常不会反复出现于同一部影片,并且还是发生在主角身上。换言之,这样的设定大概率是被默许甚至主动选择的。制作团队并非没有能力对片中的细节进行更加写实的处理,比如为卢米斯的镜架增加固定绑带,或在激烈的动作场面加入一些眼镜晃动的反馈细节。但前者无疑会损害卢米斯博爱、斯文又不失英武的形象,后者则会分散观众的注意力。此外,制作团队也可以选择让卢米斯不戴眼镜,但这似乎又不利于凸显“学者”和“技术专家”的视觉特质——就像《勇敢者游戏:决战丛林》中道恩·强森扮演的“勇石博士”,虽然设定为考古学家,但其形象却难以让人把他与学者联系到一起。于是,制作团队选择略过眼镜的细节处理,通过叙事将人们的注意力“缝合”到故事中,让观众无暇他顾,从而忽视此类细节的滑稽与突兀。
卢米斯及其眼镜所呈现的是一种持恒的“坚固”。这种“坚固”不属于影片本身,而属于好莱坞,属于好莱坞百年来主导世界电影市场的“银幕梦幻”。这是一种叙事模式和制片体系的“坚固”。它们信奉的,是平滑、连贯、凝练、完整的叙事法则,一切服务于引导观众更好地沉浸于“故事”之中,充分发挥电影的造梦功能。这也正是“梦工厂”成为好莱坞代名词的缘由。百余年来,这一系统已经生产了无数同质化的“类型电影”和“系列电影”,《侏罗纪世界:重生》就是其中之一。
归根结底,卢米斯的眼镜是被好莱坞的“无缝剪辑系统”而非物质世界的“重力法则”所支配的。在此意义上,好莱坞电影是固化的、强势的,乃至傲慢的。在好莱坞电影中,无论生活逻辑还是自然定律,都要让位于叙事法则。叙事与生活和自然之间本非对立,无数优秀电影,包括电视剧、小说、游戏等,都已经证明三者可以和谐相处。只是在好莱坞电影,或者说狭义上的“好莱坞商业大片”中,叙事才因背负过大的资本压力而在再生产中变得日益僵化。《侏罗纪世界:重生》便是一个典型案例:片中所有的人物首先是叙事角色,然后才是社会人和自然人。在强大的惯例系统中,人物必须如符号一般统一,不能缺少任何既定“笔画”才能稳定地发挥叙事作用。因此,演员乔纳森·贝利的身体,加上眼镜、衬衣和马甲等附属物件,才共同构成了“古生物学家卢米斯”这一符号。卢米斯与眼镜本就是一个整体。
当然,对现实的傲慢并不代表完全割裂现实。在《侏罗纪世界:重生》中,卢米斯不只是一个扁平的功能性角色,还是更广泛社会语境下的技术人文主义化身。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热爱自己的专业与职业,知识渊博,道德高尚,不为金钱所动,也不畏艰难险阻;他关心恐龙、同伴,乃至全人类;他搜寻恐龙DNA,只为将其秘密公之于天下,帮助人们解决心脏病困扰。可以说,卢米斯与技术向善论高度契合,构成了一种娱乐的、神圣的、潜移默化的说服力,体现出好莱坞叙事宏大、普适的一面。强势又富有隐喻,傲慢又不失人文关怀,或许才是好莱坞电影真正的生存法则。
目前来看,好莱坞的傲慢还有足够的底蕴可以支撑,但对其他地区的电影产业而言,则须保持足够的警惕。在技术主义时代,电影的傲慢正在加速滋长,并日益普遍化。数字技术出现之前,电影依靠取景、布景、实拍等物质性手段进行制作,始终保持着对现实与自然的敬畏。数字技术出现后,借助CGI、动作捕捉、数字合成、3D建模、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电影已经可以完全脱离现实,凭想象生成内容,由此便逐渐丧失了对现实与自然的谦恭。就像在电影《黑寡妇》中,“寡姐”明明是背对爆炸冲出昏暗的走廊,但脸上的光线却始终明亮、稳定。这显然是由虚拟拍摄所导致的:背景中的爆炸是绿幕特效而非实拍,自然就无法提供真实的光线反馈。只要电影继续过度依赖和迷信技术,此类情形就注定会反复上演。
如今,电影看似正走向新的自由,但自由的极致未必不是目空一切的傲慢。是要与所有数字艺术形式共享一种新的虚拟现实本体论,还是重拾物质现实复原时代的现实主义传统?这或许是正处于技术奇点时代的电影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
(作者陈静远、何源堃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韩新媒体学院讲师)
(本文来源: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本网转发此文章,旨在为读者提供更多信息资讯,所涉内容不构成投资、消费建议。对文章事实有疑问,请与有关方核实或与本网联系。文章观点非本网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悬崖边,古生物学家卢米斯纵身一跃,将即将坠落的风神翼龙DNA取样瓶救下,自己却身陷危境:他艰难地扒住岩壁,试图爬上悬崖,但随着绳子断裂,岩石松动,只能随着落石向身后的丛林坠落。局面虽岌岌可危,但观众并不会因此感到过分紧张。毕竟,作为电影的主角之一,卢卡斯仿佛手里攥着“免死金牌”。果不其然,在随后的全景镜头中,雨林中的树木顺利托住了卢米斯,并使他刚刚好地坠入了山谷中的水潭。接着,一个富有引导意味的空镜头,随着水潭涟漪消散的节奏缓缓推向岸边。镜头甫一静止,卢米斯便骤然浮出水面,英雄归来。甚至,连脸上厚重的金属边框眼镜都不曾掉落。
以上,是《侏罗纪世界:重生》中大约四分之三处的一段情节。按照好莱坞经典的三幕式结构,此处对应的应当是第二幕结束,此后将是短暂的平静与最后的高潮。影片的发展合乎预期:当卢米斯一行人重整行囊,带着历经艰险所取得的三种恐龙DNA样本踏上归途,最后的挑战——变异恐龙的夜袭与团队内部的决裂——便接踵而至。作为“侏罗纪宇宙”的最新力作,《侏罗纪世界:重生》讲述了一个老套却标准的好莱坞冒险故事。上映不足两周,该片便跻身2025年全球票房榜前十,斩获2025年中国进口片票房冠军,展示了其在商业上的亮眼表现。
只是,对于电影而言,商业属性与艺术价值、票房业绩与口碑评价之间,往往并不存在天然的协同关系。《侏罗纪世界:重生》虽然讲了一个合格的故事,但细节上仍有诸多瑕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卢米斯的“眼镜”。在影片中,这副眼镜不仅可以承受翻滚下坠的重力和游出水潭的阻力,还能抵御大海的风浪,逃离恐龙的追捕和袭击。眼镜在全片唯一一次离开卢米斯,是他触碰到温顺的泰坦巨龙,流下激动的眼泪之后主动摘下的。卢米斯的眼镜具有一种类似游戏的设定,它的“不可掉落”属性,与《我的世界》中“击杀凋灵骷髅有1/3概率掉落煤炭”的设定,以及《黑神话:悟空》中目之所及却无法穿越的“空气墙”具有同一性。只是在游戏中,这样的设定约定俗成、合情合理,是构成游戏“规则”所必需;但在电影中,这样的设定就显得有些悖于常理。
这是电影制作团队的疏忽吗?显然不是。“穿帮”在电影中虽然并不少见,但通常不会反复出现于同一部影片,并且还是发生在主角身上。换言之,这样的设定大概率是被默许甚至主动选择的。制作团队并非没有能力对片中的细节进行更加写实的处理,比如为卢米斯的镜架增加固定绑带,或在激烈的动作场面加入一些眼镜晃动的反馈细节。但前者无疑会损害卢米斯博爱、斯文又不失英武的形象,后者则会分散观众的注意力。此外,制作团队也可以选择让卢米斯不戴眼镜,但这似乎又不利于凸显“学者”和“技术专家”的视觉特质——就像《勇敢者游戏:决战丛林》中道恩·强森扮演的“勇石博士”,虽然设定为考古学家,但其形象却难以让人把他与学者联系到一起。于是,制作团队选择略过眼镜的细节处理,通过叙事将人们的注意力“缝合”到故事中,让观众无暇他顾,从而忽视此类细节的滑稽与突兀。
卢米斯及其眼镜所呈现的是一种持恒的“坚固”。这种“坚固”不属于影片本身,而属于好莱坞,属于好莱坞百年来主导世界电影市场的“银幕梦幻”。这是一种叙事模式和制片体系的“坚固”。它们信奉的,是平滑、连贯、凝练、完整的叙事法则,一切服务于引导观众更好地沉浸于“故事”之中,充分发挥电影的造梦功能。这也正是“梦工厂”成为好莱坞代名词的缘由。百余年来,这一系统已经生产了无数同质化的“类型电影”和“系列电影”,《侏罗纪世界:重生》就是其中之一。
归根结底,卢米斯的眼镜是被好莱坞的“无缝剪辑系统”而非物质世界的“重力法则”所支配的。在此意义上,好莱坞电影是固化的、强势的,乃至傲慢的。在好莱坞电影中,无论生活逻辑还是自然定律,都要让位于叙事法则。叙事与生活和自然之间本非对立,无数优秀电影,包括电视剧、小说、游戏等,都已经证明三者可以和谐相处。只是在好莱坞电影,或者说狭义上的“好莱坞商业大片”中,叙事才因背负过大的资本压力而在再生产中变得日益僵化。《侏罗纪世界:重生》便是一个典型案例:片中所有的人物首先是叙事角色,然后才是社会人和自然人。在强大的惯例系统中,人物必须如符号一般统一,不能缺少任何既定“笔画”才能稳定地发挥叙事作用。因此,演员乔纳森·贝利的身体,加上眼镜、衬衣和马甲等附属物件,才共同构成了“古生物学家卢米斯”这一符号。卢米斯与眼镜本就是一个整体。
当然,对现实的傲慢并不代表完全割裂现实。在《侏罗纪世界:重生》中,卢米斯不只是一个扁平的功能性角色,还是更广泛社会语境下的技术人文主义化身。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热爱自己的专业与职业,知识渊博,道德高尚,不为金钱所动,也不畏艰难险阻;他关心恐龙、同伴,乃至全人类;他搜寻恐龙DNA,只为将其秘密公之于天下,帮助人们解决心脏病困扰。可以说,卢米斯与技术向善论高度契合,构成了一种娱乐的、神圣的、潜移默化的说服力,体现出好莱坞叙事宏大、普适的一面。强势又富有隐喻,傲慢又不失人文关怀,或许才是好莱坞电影真正的生存法则。
目前来看,好莱坞的傲慢还有足够的底蕴可以支撑,但对其他地区的电影产业而言,则须保持足够的警惕。在技术主义时代,电影的傲慢正在加速滋长,并日益普遍化。数字技术出现之前,电影依靠取景、布景、实拍等物质性手段进行制作,始终保持着对现实与自然的敬畏。数字技术出现后,借助CGI、动作捕捉、数字合成、3D建模、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电影已经可以完全脱离现实,凭想象生成内容,由此便逐渐丧失了对现实与自然的谦恭。就像在电影《黑寡妇》中,“寡姐”明明是背对爆炸冲出昏暗的走廊,但脸上的光线却始终明亮、稳定。这显然是由虚拟拍摄所导致的:背景中的爆炸是绿幕特效而非实拍,自然就无法提供真实的光线反馈。只要电影继续过度依赖和迷信技术,此类情形就注定会反复上演。
如今,电影看似正走向新的自由,但自由的极致未必不是目空一切的傲慢。是要与所有数字艺术形式共享一种新的虚拟现实本体论,还是重拾物质现实复原时代的现实主义传统?这或许是正处于技术奇点时代的电影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
(作者陈静远、何源堃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韩新媒体学院讲师)
(本文来源: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本网转发此文章,旨在为读者提供更多信息资讯,所涉内容不构成投资、消费建议。对文章事实有疑问,请与有关方核实或与本网联系。文章观点非本网观点,仅供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