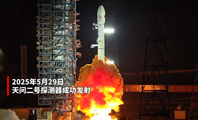舞剧《乐和长歌》以战国为历史底色,将“和国”与“乐国”的兴衰纠葛浓缩为个体命运的沉浮,在戏剧人物冲突,事件矛盾设置,人物角色塑造、舞蹈本体语言流动与舞台哲学意象的碰撞中,突破了传统战争题材的叙事框架。舞剧不局限于勾勒诱发战争的阴谋、展现战争的惨烈与颂扬和平的珍贵。而是以国君和成的价值蜕变和乐伎希音的人生救赎为主线,追问“和平如何可能”的深层命题——当权力博弈、爱恨纠缠与生命代价交织,个体的选择如何超越暴力循环,最终构建“乐和天地”的文明共识。这样的叙事深度,叙事广度,使作品从单纯的舞剧艺术呈现升华为对人类永恒困境的哲学回应。
冲突的具象化:以肢体叙事解构战争的“非理性本质”
舞剧《乐和长歌》对战争根源的剖析,并未停留在“两国对立”的表层设定,而是通过三个核心角色的肢体语言,将冲突的本质拆解为“权力异化”与“认知偏误”的双重困境。
大将戈启的人物设定及舞蹈形象充满跋扈和攻击性——一个受先王之所托而大权独揽的大将,利用安插在母后乐安身边的暗线乐伎希音的怯懦和无助来挑起和发动战争。在战前动员的男子舞蹈《战舞》表达中,舞蹈动律孔武有力,以大幅度的跳跃、有力的搏杀姿态和震地的步伐,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楚地战士的英勇气魄与战争的残酷本质。大将戈启位于舞阵中心,其肢体语言极具攻击性与扩张性,每一个动作都在彰显骄横跋扈及煽动战争的狂热。在这个雄性荷尔蒙爆棚的场域中,急促的顿点、紧绷的肩颈与直线型的肢体轨迹,不仅外化了其“尚武好战、专横跋扈”的性格,更隐喻了权力对人性的吞噬,大将戈启将战争视为巩固权位的工具,而非捍卫家国的手段,其每一次充满力量感的翻腾、旋转和跳跃,都是对“武”之本质的扭曲。
与之相对,国君和成的肢体语言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在如梦魇般的记忆碎片中,他的独白愤怒而悲怆,和成反复叩问,是谁将利刃刺入了母亲的胸膛,这时国君和成的舞姿是失衡的踉跄与紧绷的防御姿态——蒙眼的绸带不仅是视觉符号,更象征其被仇恨与猜忌遮蔽的认知。此时的和成,实则是“战争非理性”的缩影。他因个体创伤将对凶手的愤怒转嫁为对整个乐国的敌意,陷入了“以暴制暴”的逻辑陷阱。而和成作为国君,在双目受伤后一度被戈启操控,是希音的抚慰逐渐消弭了他的仇恨,也唤醒了他的理性,所以此刻国君和成与希音的双人舞蹈,极尽温婉缠绵,旋转与托举始终带着相互抚慰的质感,这样的美好场域,促使他重新审视愤怒的动机和敌对的态度,并逐渐萌发了“以乐止戈”的治国理念。
而乐伎希音的舞蹈则以“柔”破“刚”,她在与国君和成的双人舞蹈中,旋转与托举始终带着安抚的质感,在和成情绪失控时以肢体搭建“支撑”,在戈启煽动时以舞步传递“理性”,其柔弱的肢体下藏着对和成母后乐安的愧疚及生命的敬畏,此时的乐伎希音,成为对抗战争非理性的关键力量。而在女子群舞《魅影》的一段刚柔并济的舞蹈中,舞台上演员手持旌羽、身着华服的视觉华章,表面上看,它极尽楚舞之婉转柔美,翘袖折腰,翩若惊鸿,仿佛一场宫廷极乐盛宴。然而,仔细品味,便能察觉其表意上的双重性。舞者们整齐划一的动作、面具般完美的笑容,营造出一种非人化的、略带诡异的美感。这华美之下,暗藏着宫廷的虚伪、权力的倾轧与无处不在的监视。乐伎希音身处其中,她的舞蹈动作起初试图融入,但随着音乐的推进,她的动作开始出现一丝不和谐的“滞涩”与“张望”。她不再是纯粹的表演者,而是变成了一个观察者。通过她与群舞演员之间细微的动作对比——当众人沉醉于机械的华丽时,她的一个警觉的回首,一个充满疑虑的停顿——编导巧妙地外化了希音对潜伏危机的敏锐感知。这段舞蹈不仅是楚舞美学的展示,更是希音内心觉醒的开始,她开始从“乐伎”的身份中抽离,准备走向命运的暴风眼。
这种肢体叙事的精妙之处在于,它没有将战争简化为“好人与坏人”的对立,而是揭示了战争的本质是“文明底线的失守”,当权利压倒良知、仇恨覆盖理性,个体便会成为暴力的推手。正如剧中阴谋刺杀事件后,和国宫廷的集体舞蹈从有序转为混乱,舞者的肢体从协同变为冲撞,舞台灯光也从暖色转为冷暗——这不仅是场景的切换,更是对“战争摧毁文明秩序”的具象化表达。
蜕变的哲学性:和成“止戈”选择中的“大爱超越”
舞剧《乐和长歌》的核心深度,在于展现国君和成从“复仇者”到“和平守护者”的价值蜕变,这一过程并非简单的“醒悟”,而是经历了“痛苦回忆—生命代价—价值重构”的哲学思辨。双目失明的设定,在舞剧叙事中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物理视觉的丧失,迫使国君和成脱离“表象判断”(如乐国=敌人),转而以“心灵感知”去理解战争的真相。——他通过希音的温婉情感和曼妙舞步感受生命的温度,通过编钟的残响回忆和平的初衷,通过戈启的肢体张力识破权力的跋扈和阴谋。这种“失明见心”的设定,暗合了哲学中“感官遮蔽真理,心灵通达本质”的命题。为了强化国君和成思维动势的改变诱因,舞剧在这个时刻引入了一段充满楚地傩巫文化的传统舞蹈表达。这个桥段的舞蹈以祈福驱邪的巫舞姿态——如飞翔、行走、震颤、旋转、模拟鸟兽的形态——与现代舞蹈语汇融合充满了神秘感和治愈性。能够感受到此刻的国君和成正是通过这样的场域舞蹈与天地、神灵沟通。凤凰、鹤、鹿等神圣图腾通过空间调度得以完美呈现。凤凰展翅欲飞的形态,象征着重生与高洁。小鹿轻盈的跳跃,象征着对和平的灵性追求。这段舞蹈构建了国君和成的精神“净仪”,此时的他将个人的命运与天下苍生的福祉相连,其蜕变的“止戈兴乐”理念在这一刻得到了原型文化的加冕。
和成蜕变的另一个关键,在于乐伎希音向死而生的死亡。当乐伎希音在出征前以一种大无畏的牺牲来揭露戈启的阴谋。希音在出征前所跳祭祀的乐巫舞在高潮处戛然而止,肢体从铿锵有力的节奏转为轰然跌落,舞台上出征的大鼓与她扭曲的躯体形成强烈对比——这一画面并非单纯的“悲剧渲染”,而是对“和平需要代价”的哲学叩问。和平不是凭空而来,它需要有人用生命打破暴力循环,用牺牲唤醒麻木的良知。乐伎希音的自我救赎与牺牲,让国君和成彻底明白,“强”的本质不是征服,而是守护。“武”的真谛不是杀戮,而是“止戈”(正如《左传》所言“止戈为武”)。这种认知的转变,最终化为国君和成以天下苍生为重的选择。
剧中春和景明的场景,舞者以协同的肢体搭建“春意盎然”的意象,国君和成的舞步从踉跄犹疑变为开朗愉悦,他的每一次抬手都带着“生机”,每一次转身都藏着“希望”——这不再是国君的权力仪式,而是对生命的礼赞与对文明的重建。此时的和成,其“强”已超越了“尚武”的蛮力,转为“守护苍生”的大爱。他明白,一个民族的骄傲,不在于“征服多少土地”,而在于“让国民活得有尊严”。一个国君的价值,不在于“拥有多少权力”,而在于“能否守护和平的底线”。这种“大爱超越”的选择,使和成的形象脱离了“君主”的身份局限,成为人类对和平永恒渴望的象征。
隐喻的文明性:“乐和天下”与人类和平的永恒追求
舞剧《乐和长歌》的尾声,舞台上出现布满稻穗的《丰收》群舞,这不再是《魅影》的诡谲或《战舞》的肃杀,而是两国人民在钟声中和乐共舞的“国泰民安”景象,象征着“止戈兴乐”的愿景终于实现。当金黄稻穗铺满舞台,编钟奏响平和的旋律,“乐和天下”的主题不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化为可感知的文明意象——稻穗象征“生”,编钟象征“和”,二者的结合,暗合了人类文明的核心诉求。以和平守护生命,以文明对抗蛮横。这种意象的选择,具有深刻的文明隐喻。战争的本质是“破坏生命”(如剧中索魂的骷髅舞象征杀戮与死亡),而和平的本质是“滋养生命”(如稻穗代表的丰收与安宁)。编钟作为“乐”的载体,不仅是乐器,更是文明的符号——它需要不同的钟体协同发声,正如和平需要不同的国家、民族协同守护。“乐和天下”的理念,在剧中超越了“和国与乐国”的地域局限,成为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思考。
舞剧《乐和长歌》通过国君和成的选择及乐伎希音的牺牲,告诉今日的观众,任何文明的延续,都不能依赖“强悍与凶狠”,而必须建立在“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尊重、对正义的捍卫”之上——如果失去这些文明底线,再古老的历史也只是“蛮荒的重复”。正如剧中编钟的旋律,它不是某一个国家的声音,而是人类共同的和平之音,满台的稻穗,不是某一个民族的丰收,而是人类共同的生命希望。这种文明隐喻的价值,在于它让《乐和长歌》超越了“历史剧”的范畴,成为对当下世界的回应。在当今仍有冲突与战乱的时代,舞剧通过舞蹈本体语言的肢体与哲学意象的结合,提醒我们,和平不是“理所当然”,它需要每一个国人的守护。文明不是“固步自封”,它需要不同群体的协同构建。正如国君和成最终明白的那样,“乐和天地”不是遥不可及的理想,而是藏在每一次“拒绝暴力”的选择中,藏在每一次“守护生命”的行动里——这是舞剧留给观众最深刻的哲学启示,也是“藏在舞步里的大国大爱”的真正内涵。
疆嘎:国家一级编导
云南省舞蹈家协会副主席
云南省舞蹈家协会理论评论委员会主任
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昆明舞蹈家协会主席
2025年10月11日
舞剧《乐和长歌》以战国为历史底色,将“和国”与“乐国”的兴衰纠葛浓缩为个体命运的沉浮,在戏剧人物冲突,事件矛盾设置,人物角色塑造、舞蹈本体语言流动与舞台哲学意象的碰撞中,突破了传统战争题材的叙事框架。舞剧不局限于勾勒诱发战争的阴谋、展现战争的惨烈与颂扬和平的珍贵。而是以国君和成的价值蜕变和乐伎希音的人生救赎为主线,追问“和平如何可能”的深层命题——当权力博弈、爱恨纠缠与生命代价交织,个体的选择如何超越暴力循环,最终构建“乐和天地”的文明共识。这样的叙事深度,叙事广度,使作品从单纯的舞剧艺术呈现升华为对人类永恒困境的哲学回应。
冲突的具象化:以肢体叙事解构战争的“非理性本质”
舞剧《乐和长歌》对战争根源的剖析,并未停留在“两国对立”的表层设定,而是通过三个核心角色的肢体语言,将冲突的本质拆解为“权力异化”与“认知偏误”的双重困境。
大将戈启的人物设定及舞蹈形象充满跋扈和攻击性——一个受先王之所托而大权独揽的大将,利用安插在母后乐安身边的暗线乐伎希音的怯懦和无助来挑起和发动战争。在战前动员的男子舞蹈《战舞》表达中,舞蹈动律孔武有力,以大幅度的跳跃、有力的搏杀姿态和震地的步伐,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楚地战士的英勇气魄与战争的残酷本质。大将戈启位于舞阵中心,其肢体语言极具攻击性与扩张性,每一个动作都在彰显骄横跋扈及煽动战争的狂热。在这个雄性荷尔蒙爆棚的场域中,急促的顿点、紧绷的肩颈与直线型的肢体轨迹,不仅外化了其“尚武好战、专横跋扈”的性格,更隐喻了权力对人性的吞噬,大将戈启将战争视为巩固权位的工具,而非捍卫家国的手段,其每一次充满力量感的翻腾、旋转和跳跃,都是对“武”之本质的扭曲。
与之相对,国君和成的肢体语言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在如梦魇般的记忆碎片中,他的独白愤怒而悲怆,和成反复叩问,是谁将利刃刺入了母亲的胸膛,这时国君和成的舞姿是失衡的踉跄与紧绷的防御姿态——蒙眼的绸带不仅是视觉符号,更象征其被仇恨与猜忌遮蔽的认知。此时的和成,实则是“战争非理性”的缩影。他因个体创伤将对凶手的愤怒转嫁为对整个乐国的敌意,陷入了“以暴制暴”的逻辑陷阱。而和成作为国君,在双目受伤后一度被戈启操控,是希音的抚慰逐渐消弭了他的仇恨,也唤醒了他的理性,所以此刻国君和成与希音的双人舞蹈,极尽温婉缠绵,旋转与托举始终带着相互抚慰的质感,这样的美好场域,促使他重新审视愤怒的动机和敌对的态度,并逐渐萌发了“以乐止戈”的治国理念。
而乐伎希音的舞蹈则以“柔”破“刚”,她在与国君和成的双人舞蹈中,旋转与托举始终带着安抚的质感,在和成情绪失控时以肢体搭建“支撑”,在戈启煽动时以舞步传递“理性”,其柔弱的肢体下藏着对和成母后乐安的愧疚及生命的敬畏,此时的乐伎希音,成为对抗战争非理性的关键力量。而在女子群舞《魅影》的一段刚柔并济的舞蹈中,舞台上演员手持旌羽、身着华服的视觉华章,表面上看,它极尽楚舞之婉转柔美,翘袖折腰,翩若惊鸿,仿佛一场宫廷极乐盛宴。然而,仔细品味,便能察觉其表意上的双重性。舞者们整齐划一的动作、面具般完美的笑容,营造出一种非人化的、略带诡异的美感。这华美之下,暗藏着宫廷的虚伪、权力的倾轧与无处不在的监视。乐伎希音身处其中,她的舞蹈动作起初试图融入,但随着音乐的推进,她的动作开始出现一丝不和谐的“滞涩”与“张望”。她不再是纯粹的表演者,而是变成了一个观察者。通过她与群舞演员之间细微的动作对比——当众人沉醉于机械的华丽时,她的一个警觉的回首,一个充满疑虑的停顿——编导巧妙地外化了希音对潜伏危机的敏锐感知。这段舞蹈不仅是楚舞美学的展示,更是希音内心觉醒的开始,她开始从“乐伎”的身份中抽离,准备走向命运的暴风眼。
这种肢体叙事的精妙之处在于,它没有将战争简化为“好人与坏人”的对立,而是揭示了战争的本质是“文明底线的失守”,当权利压倒良知、仇恨覆盖理性,个体便会成为暴力的推手。正如剧中阴谋刺杀事件后,和国宫廷的集体舞蹈从有序转为混乱,舞者的肢体从协同变为冲撞,舞台灯光也从暖色转为冷暗——这不仅是场景的切换,更是对“战争摧毁文明秩序”的具象化表达。
蜕变的哲学性:和成“止戈”选择中的“大爱超越”
舞剧《乐和长歌》的核心深度,在于展现国君和成从“复仇者”到“和平守护者”的价值蜕变,这一过程并非简单的“醒悟”,而是经历了“痛苦回忆—生命代价—价值重构”的哲学思辨。双目失明的设定,在舞剧叙事中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物理视觉的丧失,迫使国君和成脱离“表象判断”(如乐国=敌人),转而以“心灵感知”去理解战争的真相。——他通过希音的温婉情感和曼妙舞步感受生命的温度,通过编钟的残响回忆和平的初衷,通过戈启的肢体张力识破权力的跋扈和阴谋。这种“失明见心”的设定,暗合了哲学中“感官遮蔽真理,心灵通达本质”的命题。为了强化国君和成思维动势的改变诱因,舞剧在这个时刻引入了一段充满楚地傩巫文化的传统舞蹈表达。这个桥段的舞蹈以祈福驱邪的巫舞姿态——如飞翔、行走、震颤、旋转、模拟鸟兽的形态——与现代舞蹈语汇融合充满了神秘感和治愈性。能够感受到此刻的国君和成正是通过这样的场域舞蹈与天地、神灵沟通。凤凰、鹤、鹿等神圣图腾通过空间调度得以完美呈现。凤凰展翅欲飞的形态,象征着重生与高洁。小鹿轻盈的跳跃,象征着对和平的灵性追求。这段舞蹈构建了国君和成的精神“净仪”,此时的他将个人的命运与天下苍生的福祉相连,其蜕变的“止戈兴乐”理念在这一刻得到了原型文化的加冕。
和成蜕变的另一个关键,在于乐伎希音向死而生的死亡。当乐伎希音在出征前以一种大无畏的牺牲来揭露戈启的阴谋。希音在出征前所跳祭祀的乐巫舞在高潮处戛然而止,肢体从铿锵有力的节奏转为轰然跌落,舞台上出征的大鼓与她扭曲的躯体形成强烈对比——这一画面并非单纯的“悲剧渲染”,而是对“和平需要代价”的哲学叩问。和平不是凭空而来,它需要有人用生命打破暴力循环,用牺牲唤醒麻木的良知。乐伎希音的自我救赎与牺牲,让国君和成彻底明白,“强”的本质不是征服,而是守护。“武”的真谛不是杀戮,而是“止戈”(正如《左传》所言“止戈为武”)。这种认知的转变,最终化为国君和成以天下苍生为重的选择。
剧中春和景明的场景,舞者以协同的肢体搭建“春意盎然”的意象,国君和成的舞步从踉跄犹疑变为开朗愉悦,他的每一次抬手都带着“生机”,每一次转身都藏着“希望”——这不再是国君的权力仪式,而是对生命的礼赞与对文明的重建。此时的和成,其“强”已超越了“尚武”的蛮力,转为“守护苍生”的大爱。他明白,一个民族的骄傲,不在于“征服多少土地”,而在于“让国民活得有尊严”。一个国君的价值,不在于“拥有多少权力”,而在于“能否守护和平的底线”。这种“大爱超越”的选择,使和成的形象脱离了“君主”的身份局限,成为人类对和平永恒渴望的象征。
隐喻的文明性:“乐和天下”与人类和平的永恒追求
舞剧《乐和长歌》的尾声,舞台上出现布满稻穗的《丰收》群舞,这不再是《魅影》的诡谲或《战舞》的肃杀,而是两国人民在钟声中和乐共舞的“国泰民安”景象,象征着“止戈兴乐”的愿景终于实现。当金黄稻穗铺满舞台,编钟奏响平和的旋律,“乐和天下”的主题不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化为可感知的文明意象——稻穗象征“生”,编钟象征“和”,二者的结合,暗合了人类文明的核心诉求。以和平守护生命,以文明对抗蛮横。这种意象的选择,具有深刻的文明隐喻。战争的本质是“破坏生命”(如剧中索魂的骷髅舞象征杀戮与死亡),而和平的本质是“滋养生命”(如稻穗代表的丰收与安宁)。编钟作为“乐”的载体,不仅是乐器,更是文明的符号——它需要不同的钟体协同发声,正如和平需要不同的国家、民族协同守护。“乐和天下”的理念,在剧中超越了“和国与乐国”的地域局限,成为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思考。
舞剧《乐和长歌》通过国君和成的选择及乐伎希音的牺牲,告诉今日的观众,任何文明的延续,都不能依赖“强悍与凶狠”,而必须建立在“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尊重、对正义的捍卫”之上——如果失去这些文明底线,再古老的历史也只是“蛮荒的重复”。正如剧中编钟的旋律,它不是某一个国家的声音,而是人类共同的和平之音,满台的稻穗,不是某一个民族的丰收,而是人类共同的生命希望。这种文明隐喻的价值,在于它让《乐和长歌》超越了“历史剧”的范畴,成为对当下世界的回应。在当今仍有冲突与战乱的时代,舞剧通过舞蹈本体语言的肢体与哲学意象的结合,提醒我们,和平不是“理所当然”,它需要每一个国人的守护。文明不是“固步自封”,它需要不同群体的协同构建。正如国君和成最终明白的那样,“乐和天地”不是遥不可及的理想,而是藏在每一次“拒绝暴力”的选择中,藏在每一次“守护生命”的行动里——这是舞剧留给观众最深刻的哲学启示,也是“藏在舞步里的大国大爱”的真正内涵。
疆嘎:国家一级编导
云南省舞蹈家协会副主席
云南省舞蹈家协会理论评论委员会主任
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昆明舞蹈家协会主席
2025年10月11日